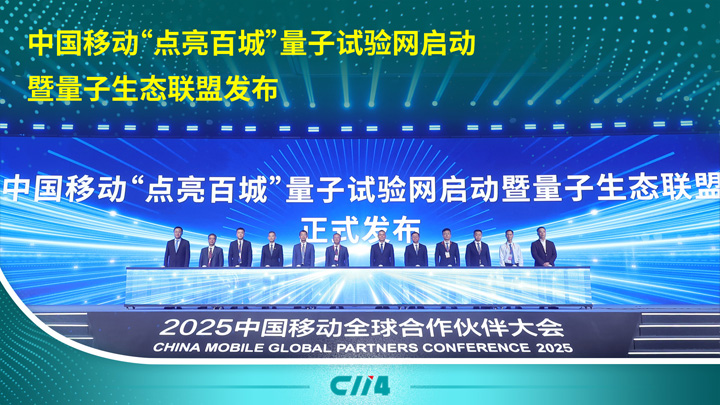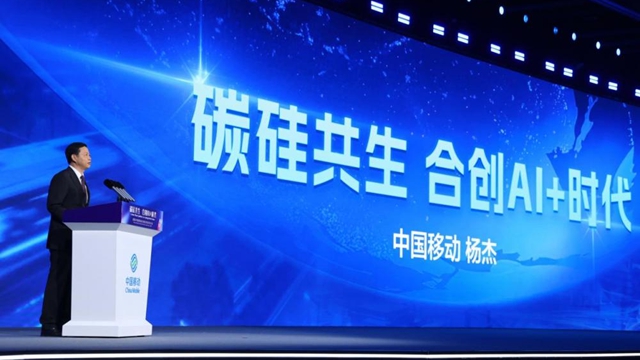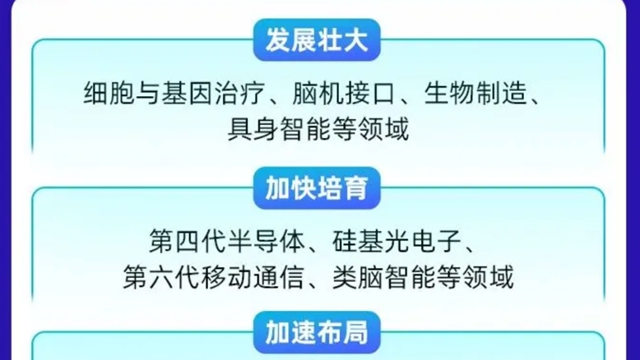真正能够决定成都、重庆在下一个十年中位置的,不是各种耀眼的数字,而是能否妥善处理三个“很西部”的难题:即能否实现“民富”,推进城乡统筹;如何定位在产业承接中的角色;怎样激发民营经济活力?
西部大开发是一场马拉松,参与其中的“队员”,耐力比爆发力更关键。在两个十年的交汇点上,西部各城市都设计了一套新标签。例如在金融领域,重庆提出要做“长江上游金融中心”,成都亮出了“典型中国西部之心”的城市定位,打造“西南区域金融中心”。其它西部内陆省会城市,如贵阳、昆明、兰州,已不在第一阵营之中。真正能够决定它们在下一个十年中位置的,不是各种耀眼的数字,而是能否妥善处理三个“很西部”的难题:即能否实现“民富”,推进城乡统筹;如何定位在产业承接中的角色;怎样激发民营经济活力。
民富问题重要,是因为西部都有地域广阔的农村,最能说明发展状态的不是GDP,而是人均GDP。
重庆工业基础最扎实,但农村包袱最重,所谓大城市带农村,其实是小马拉大车,而且还要面对库区移民问题,局面复杂。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一直是统筹重点。成都周边农村以平原为主,没有自然阻隔,城市与农村社会联系紧密,两者人口也基本相当,压力比重庆小得多,是“大马拉小车”。成都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孙平将统筹策略总结为八个字:“还权赋能、农民自主”,即将农民的权力还给农民,然后通过统筹让土地财富的能量发挥出来。
再看产业承接。金融危机后,产业西移已渐成大趋势。可二座城市也都意识到资源优势和成本优势难以长期持续,刻意回避再走沿海的老路,都特别青睐资金密集与技术密集型企业。
重庆的机械、化学、汽车摩托车、材料等工业根基深厚,劳动力资源丰富,但产业链不完整,与围绕市中心的“一小时经济圈”相比,“两翼”欠发达地区引资能力十分薄弱,严重失衡。它调整经济结构的愿望最迫切。成都工业基础薄弱,大型工业产品物流能力差,但胜在气质温婉秀丽,科技人才数量在西南地区首屈一指。近年成都放大、巩固软实力,同时注重“硬”发展,建立了亚洲最大的铁路集装箱中心站,提高自身的物流能力,努力发展高端产业和产业高端。拥有世界 500强的数量、外国领事馆数量、外资银行和外资保险机构的数量、拥有国际航线的数量都居中西部榜首。
政府是重庆经济运行中的主角,从管理、指导为主过渡到服务为主,是其面临的挑战。重庆民企活力旺盛,可总体上处于传统低端产业和粗放型增长状态。成都民营经济则十分活跃,特别是小企业生机勃勃。成都常务副市长孙平谈到,成都是60万家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支撑了大半个江山,这是最大的财富。
难能可贵的是,成都已经主动跳出“市”的局限,与近邻简阳市、资阳市签订合作协议,承担起区域中心城市辐射职能,统一电话区号、统筹区域发展,在区域一体化中早走一步。从“西部之心”需要的对周边城市和区域的带动力上比较,成都胜出一筹。
然而,即便成都已经在以上多个方面领跑西部,但要作为“西部之心”承担对整个西部区域的辐射带动作用,成都还需努力。
成都:西部之心
成都将“软”字诀演绎得炉火
纯青:看似“绵软”实则内蓄刚劲,这是它最独特的竞争力
文 | 本刊记者 何伊凡
古人拆“蜀”字,为“四”面围起来的一条虫,川人在盆地内是虫,只有走出门,方有望成龙。
新希望(15.17,1.38,10.01%)集团董事长刘永好曾同意这一说法,他记得二十年前,孔雀东南飞,以成都为甚。“高端人才去了,农民工去了,不但人去了,企业也去了。国有企业去了,民营企业去了,带动着大小项目都去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成都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的存款,在西部吸收,要拿到沿海去发”。
如今,他看到了新格局。“我的几位好朋友,例如马云,过去他们不怎么谈成都,甚至也不怎么谈西部,现在都开始在成都布局。”几个月前,他去台湾,郭台铭请他吃饭,双方聊到虽然产业相差甚远,可富士康国内最大投资项目已经确定落子成都,未来双方在成都也有合作的可能。
越来越多的“龙”盘踞到天府之国,世界500强中有175家落户,类似成绩可以列成一张长长的名单。9月初,台湾电机电子工业同业公会公布《大陆地区投资环境与风险调查》报告,经过对中国内地1998个城市的筛选,成都紧随昆山、上海之后,成为台商未来最想投资的城市。
西部大开发十年后,成都出现了两条脉络:它有中国最多的茶馆;它是中国最大的宠物市场之一;它是中国最大的诗歌码头;它是全球离冰川最近的人口过千万大城市;它能把回锅肉做出一千种口味。另一方面,它的金融后台数量全国第一;出口总额居中西部首位;是中国四大交通枢纽之一;机场旅客和货物吞吐量均列西部榜首;是全国最大的蔬菜和生猪生产基地。这两条脉络联接在一起,勾勒出独特的“成都模式”。它的精致、悠闲、淡泊、宽容,与快速崛起的雄心不断摩擦、碰撞,形成新动力,令这个缺乏矿产资源、工业基础、港口优势的城市脱颖而出。
成都常务副市长孙平还记得,十年前做西部大开发规划时,市委采用了西部“战略高地”的提法,“当时感觉还比较冒昧,如今回过头来看,我(说这话)的底气已经很足了。”与他这个说法互为注脚的是,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牛文元在接受央视新闻联播记者采访时表示,由于成都对西部地区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堪称“西部之心”。
软环境
2010年4月,“船王”马士基集团旗下的物流公司丹马士迁入成都,办公面积近1万平方米,号称其全球最大办公室。迁移并没有给丹马士供应链总监冯慧敏带来丝毫不适。她的丈夫曾在四川大学读书,经常和她谈起成都如何“来了就不想走”。如今身临其境,她体会到其中的含义。“在深圳每次从飞机场一出来,就不知道为什么觉得浮躁,着急、上火。在成都就不会这样。虽然路上堵车,司机也不会拼命按喇叭催你。”
实际上,她并没有多少时间细细品味成都,因为搬迁后挑战性更强,可她并没有感觉焦灼。“我和同事们分享这种感觉,都说不清为什么,或许因为每天见到的人都是笑眯眯的吧。”
不要说“客家人”,生长于斯的刘永好也深有感受。新希望产业遍布全国,但他从未想过把总部搬离成都。“很多人觉得成都太休闲,不适宜创业,其实不对,这里人心态好,做事比较安心。该打麻将打麻将,该工作就工作,社会环境像火锅一样,什么都放进来煮,大家围在一起和和气气的吃。”
这种深入骨髓的文化积淀,其它城市无法复制。明末以来成都历经屠城血洗,一度十室九空,成为一片废墟,近代三百多年又曾出现四次大移民。几番沉浮,它有顽强的生命力,也有海纳百川的气度。
成都的另一种“软”,是优秀而廉价的人才蓄水池。抗战时期北方27座大学迁到成都,三线建设时期大批电子通信行业人才也集中于此,它有42座高校,在校大学生近60万人,是西南地区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最集中的城市。“在其它西部城市的酒吧,几乎听不到有人说英语,但成都的酒吧与茶馆,有时会像大学的英语角一样。”重庆贝特投资公司董事董竹奔波于西部各大城市,对此颇有感触。
选择成都,是丹马士全球最大一次搬迁,几乎把其在深圳、青岛等沿海城市的相关业务全都搬了过来。“所有的搬迁流程文件上规定得一清二楚,就像《杜拉拉升职记》里说的,先迈左脚先迈右脚都帮你设计好了。”真正让冯慧敏忧心的是,能否在短时间内招募到所需的人才。
丹马士对人才要求颇高,它有一套著名的马士基性格测试和IQ测试,江湖传言在沿海地区通过率也不足10%。然而来成都后,这恰恰成了最令她轻松的环节。丹马士的目标是组建千人左右的团队,半年多时间就招募了890多人。冯慧敏评价成都本地大学生整体素质与沿海没有差别,接下来的培训中,觉察到他们的付出精神、团队精神更加突出。跨国公司在成都组建团队,都有类似感受。
唯一令他们惊讶的是这里的“孩子们”观念更保守。某公司高层记得,与毕业生签合同时,对方吓坏了,觉得这么大的事怎么能坐下来马上就签呢?一定要拿回去和爸爸妈妈商量一下。不过他也发现,恰恰由于保守,成都的员工稳定性最强,轻易不会跳槽。
对成都之“软”体会最深的,莫过于动漫、游戏产业。哆可梦网络科技公司的两款网游产品尚未上线运营,以投资规模计,已是成都最大的游戏公司。走进该公司,就看到300多个年轻人带着耳机忙碌在开放的工作台前。公司副总裁皮大福介绍,他们最初也曾考虑将总部设在北京或者上海,但最终还是选择了成都。这里的人文环境适合做创意产业,而且游戏行业各层面人才都具备。几所高校提供了足够的IT和美术人才,又有大量的小游戏公司,单独每家研发能力虽然不均衡,可构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已成为游戏外包的基地。各大游戏公司中有许多中高层是四川人,如今有回家乡发展的意愿,他最近就挖来好多人。
“对一个游戏公司来说,你所希望的一切都在这里。”皮大福挥了一下手,窗外,能看到完美时空、腾讯、巨人,以及日韩一线游戏公司的LOGO。这里还有英特尔的世界工厂、阿里巴巴西部基地等等,成都已经成为中国IT产业增长“第四极”。
“软”是成都的灵魂,在漫长的岁月里,它曾只在生活中发酵,而如今成为变革中的竞争力。
软调控
在深圳等东南沿海发达地区,政府对经济的调控接近隐遁无形,在内陆,政府往往强力介入,主导着招商引资、产业规划、金融支持等领域的走向。成都的风格介于两者之间,明朗直接,但并不强硬。
坐在“海棠晓月”茶楼的二层,俯瞰宽窄巷子,细雨梧桐,青苔石板,每一个细节处均可咀嚼出韵味,顿生“时间就是用来浪费”之感。成都文旅集团董事长尹建华端起茶杯,环视着自己的产品,叩着茶碗说,“这里就是成都。”
文旅集团是成都市政府“软调控”的典型产物,而宽窄巷子是其第一个项目。2007年3月,文旅集团组建之初市政府内部也有不同意见,反对者认为国有企业进入这个领域没有必要,支持者认为成都正在服务业升级关键阶段,需要国有资本拉动。该集团最终定位于做“大旅游”,将文化与旅游结合,对一些需要大量基础投入、市场不成熟的区域进行开发运营,同时也为城乡统筹提供支撑。
宽窄巷子是清代兵丁胡同,为北方民居在川西的影子,本已破败,属于旧城改造范畴。文旅集团接手后投资达6个亿,复旧如旧,将成都的吃喝玩乐、消费业态都捕捉进来。尹建华认为,如果民营企业做这样的项目,一方面投资庞大,另一方面为尽快收回投资,可能注入太多商业元素,把味道就破坏了。
文旅集团招商中,别出心裁请来文化人开店,诗人翟永明、石光华、李亚伟等都在这里开了酒吧或餐厅。随便走出一位“店家”,可能就是雕塑、国画或者民俗文化研究的大家。 虽是“政府项目”,可宽窄巷子2010年市场估值不下于15个亿。之后的西岭雪山、大慈寺、水井坊(22.74,-0.18,-0.79%)等项目,都延续了类似思路。外地投资者看到了其中的潜力,蜂拥而至,香港太古集团等已与文旅集团签订合作协议。
2010年4月,张五常来到成都,称赞宽窄巷子是他见过的“搞旧文化消闲最高明的地方”。他随后写了一篇《从成都学得的创作定律》的博文,谈到了政府对市场要素的干预。“成都市政府有计划地推出了不少建设项目,论配套,一般搞得好-非常好。这是违反了弗里德曼当年之见:他认为政府策划的发展比不上市场的运作,一般失败。”
为了搞清楚答案,他多停留了一天,去拜访常务副市长孙平。他提出几个成都的政府项目,问权利的结构。第一项就是大名鼎鼎的天府软件园,他问对方软件园是否算成功的政府投资,本以为孙平会说:“当然!”殊不知对方回答:“很难说,还要多等多看。”孙平显然认为财政上该项目还没有打平,而增加就业的间接利益不容易算得准。张五常由此认为政府投资的成败准则也以市场来评价,但不单纯以市场评价,显然是走出弗里德曼推断的原因之一。
在招商引资中,“软调控”亦大有用武之地。成都负责招商引资的部门是“投资促进委员会”,简称投促委,无论职能还是名称,在全国都无先例。这一改变是引资思路调整的投射。据投促委副主任周密介绍,成都早期负责招商的有三个部门外经委、经协办与招商局,带有一定计划经济时期色彩。2006年成都市主要官员出访爱尔兰,受到爱尔兰“工业促进署”的触动,开始筹备该机构。
和许多内陆城市一样,成都每一个区(市)县过去都在自己招商,村村点火,各自为政,互相之间有竞争,产业定位不明晰。投促委成立后,招商之外增加了一项统筹和规划功能,从2008年进行“一区一主业”,新企业按照分类入园,老企业逐步调整。目前,成都市与周边的资阳、雅安、眉山、德阳等地市建有 5个产业功能合作区。周密介绍,对于不符合成都市产业定位的项目,成都市将按照合作区协议进行项目转移。这被认为是成都主动开始向周边辐射,带动成都经济区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
这隐含了一种“外软内硬”的招商思路:对企业保持热情,对政府严格控制。据国家统计数据,2010年1-7月,成都实际使用外资22.9993 亿美元,同比增长25.2%,位居西部城市第一位。连夜准备引资材料,主要官员三顾茅庐之类的招商事迹,在许多城市都曾上演,成都也不乏这样的桥段,但它一系列迎合市场规律的引资思路可能扮演着更重要角色。
“我去过西部的每一个大城市,成都是唯一在谈判中和我们说‘不’的政府。”一位跨国电子企业负责人告诉本刊,“他们会说,‘我们确实不具备某项条件’或者‘这项优惠是我们无法提供的’,但同时会展示最具优势的物流网络、服务体系,这样反而让我们觉得,用中文来表达就是‘靠谱’。”
对政府之手的力道,民营经济最为敏感。成都民营企业的特点是规模以下的小企业星罗棋布。虽然同样面临金融瓶颈等难题,但他们在中西部民营经济体中依然最为活跃,在城乡统筹、公共建设等领域,成都也对民营企业打开了一些通道。
“我所倾向的观点是,企业要做企业的事,政府要做政府的事,大家各忙各的,政府对企业的影响和干预除非万不得已,尽量不要插手太多。”成都大型民营企业通威集团董事长刘汉元说,他认为在此方面,成都市政府做的不错。“它很慎用公权力的优势,主要着力在资源维护和基础服务上。”
软硬兼施
应该继续“软下去”还是要“硬起来”?“软”与“硬”之间的比例如何搭配?是成都一直辩证思考的问题。
与重庆不同,成都最初没有自己的工业体系。孙平记得,解放时成都的工业只有“三根半烟筒”—其中有一家肥皂厂是不冒烟的,因此只算半根。后来30年,成都加快工业化进程,跟重庆的差距缩小了。
但成都发展究竟以什么作为核心竞争力?2008年底市委工作会议公开提出来一个现代产业体系的概念,要把总部基地和现代服务业作为产业体系核心,以高新技术为先导,以现代制造业和现代农业为支撑。
这一图景在2009年进一步明晰,提出成都要建设为“世界现代田园城市”,在此概念下,第三产业自然成为主角。“服务业是在备受歧视的情况下茁壮成长的,与工业比只是小媳妇。在这种大背景下成都服务业仍能比较快速地成长,有理由对它寄予厚望。”孙平说。
不过,工业依然是成都经济的底本,只是它的口味将变得“挑剔”,专注“高端产业”与“产业高端”,前者主要为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包括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物联网、云计算、生物医药、航空等。而产业高端,则主要针对传统产业而言,成都要着力发展的产业高端着眼于自身基础,包括汽车、石化、冶金建材、食品、制鞋及皮革、家具等传统自身优势产业。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使企业通过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实现产业的价值链高端化。
以前印象中汽车整车项目主要在重庆,成都做配套;但走进成都市龙泉驿区的汽车产业综合功能区,如同进入了一座汽车城。一汽、大众、丰田、神钢、卡特彼勒、南车、三一重工(27.08,0.72,2.73%)等公司等比邻而居。江森、麦格纳、德尔福、富奥、华翔等零配件配套企业,九峰国际、美国帅车、陆捷物流等服务企业簇拥在周围。吉利厂区占地达1000多亩,大片土地刚刚翻开,正在建设中。
“从产量上看,我们与重庆依然有差距,可车型和产业链都很完整,布局已经打开了。”市经委主任何礼颇为自豪。除建成中国第一高端商务车(中巴) 生产基地外,成都正努力帮助一汽大成都基地新速腾、新捷达扩产,目标是建成中国轿车百万辆生产基地。丰田新普拉多、吉利全球鹰系列等SUV项目目标是年产 20万辆以上,将巩固“成都造SUV”全国领先地位。
这是成都“硬”产业的一个注脚,它瞄准的不仅是整车,还有“硬”中的“软”,如汽车贸易、汽车娱乐、汽车研发,已经有一套规划,并且尝试过“汽车文化周”与全国超级卡车大赛总决赛等活动。
2010年初,国家信息中心公布了蒙代尔和厉以宁牵头的《西部大开发中的城市化道路—成都的城市化模式案例研究》的报告,两人联袂推介成都是西部大开发的引擎城市。将成都与芝加哥类比,认为成都面临着类似芝加哥在上世纪60-70年代经济转型时期的内外环境,成都要浓缩芝加哥从早期工业化到中期去工业化再到建设全球城市、信息城市的百年历程,行走在“软”与“硬”之间,它需要艰难摸索。
“认清一条道路不容易,坚持一条道路就更难。”成都常务副市长孙平说,“软与硬,这些问题每时每刻都有冲突,至今仍在不断调整与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