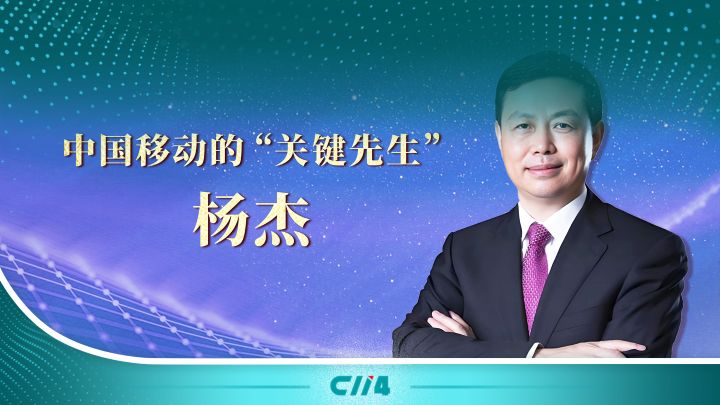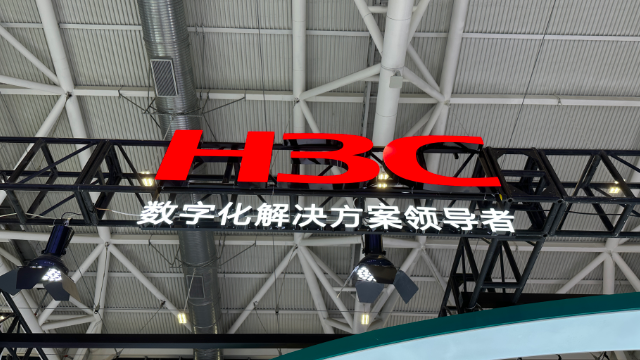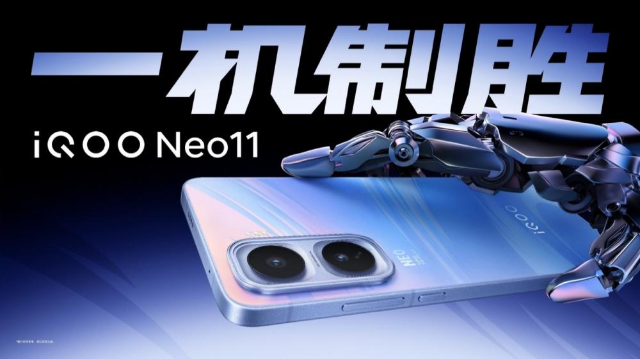在喧嚣的网络时代,卡尔的这本书无疑是一服清醒剂。
7年前,时任《哈佛商业评论》执行主编的尼古拉斯.卡尔,以一篇《IT不再主要》的文章,在IT界引起轩然大波。在他看来,在电脑与网络技术已经与电力、铁路等工业时代的基础设施一样满世界都是的时候,宣扬IT可以带来竞争优势,“即便不是不可能,也非常困难”。
这一次,尼古拉斯.卡尔瞄准的是数字化的“内容”,或者说是互联网背景下人们的“阅读”行为。
卡尔认为,“信息过载”已经不是虚张声势的提醒,而是令人烦躁不安的事实。这个事实不但在吞噬着你我的注意力,更重要的是我们已经“失去了以前的大脑”——这是个非常要命的问题。
那,以前的大脑是什么样子的?
在这本书里,卡尔历数人的大脑在语音时代、文字时代,以及古腾堡印刷术发明之后,大批量书籍报刊传播时代的差异,他不厌其烦地引证大量神经生理学、文化发展史的文献,为的是说明这样一件事情:
人的大脑是高度可塑的。
“人的大脑是高度可塑的”,当然,这种可塑性,人自身是察觉不到的。不过今天,你终于“察觉”到了:你时常会觉得耳鸣、目涩,注意力无法集中;你懒于记忆,习惯于张口就问;你不喜欢冗长的陈述和表白,喜欢直奔主题和搜寻答案。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心理学教授杰弗里.施瓦茨把这种状态称为“忙者生存”。
正如经济学家泰勒.考恩所说:“在能够轻易获得信息的情况下,我们通常喜欢简短、支离破碎而又令人愉快的内容。”
这种“非线性”阅读方式,或者说支离破碎的浏览方式,一方面是人们应对信息过载的无奈之举,另一方面也是人的大脑神经系统在悄然变化的直接证据。
卡尔说:“从纸面转到屏幕,改变的不仅是我们的阅读方式,它还影响了我们投入阅读的专注程度和沉浸在阅读之中的深入程度。”
互联网的出现,正在彻底颠覆书籍所养成的阅读习惯。由于互联网越来越多地发挥着知识记忆的功能,使得人的大脑对博闻强记的依赖迅速减弱;此外,图书馆、书籍所培育出来的“宁静的阅读”和“深邃辽远的对话”,在社交媒体的喧嚣声中,也成为无法还原的田园景象。
卡尔很忧虑地说:“我们已经抛弃了孤独宁静、一心一意、全神贯注的智力传统,而这种智力规范正是书籍赠与我们的。我们已经把自己的命运交到了杂耍者的手上。我们正在彻底颠覆图书好不容易缔造出来的“深阅读”、独处阅读的氛围和神经系统。”
这本书的绝大部分叙述,不由得让人产生沮丧、无助的感觉。
在日益强大的计算机器和联网机器面前,人们一方面欢呼雀跃,另一方面又满腹狐疑。诚如尼葛洛庞帝所预言的那样,数字化不只是与计算有关,它决定着人类的生存——这一天已经日渐清晰、日益真实了。
不过在这本书里,卡尔的字里行间,仍然在坚守着那些“最不可能计算机化的部分”,他把这种依赖互联网记忆的生存状态称为“记忆外包”,并且给出了自己的惊人论断:
记忆外包,文明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