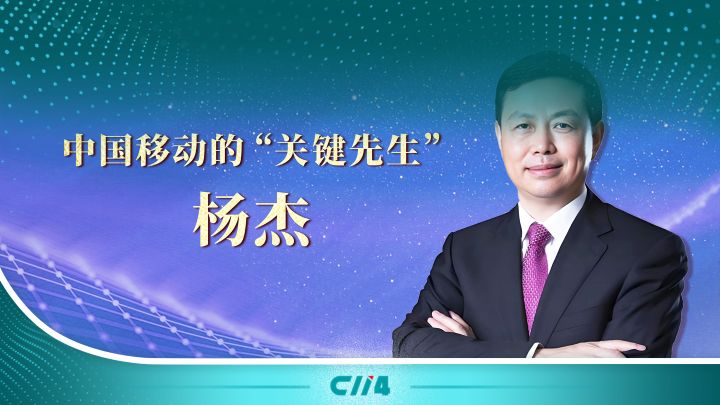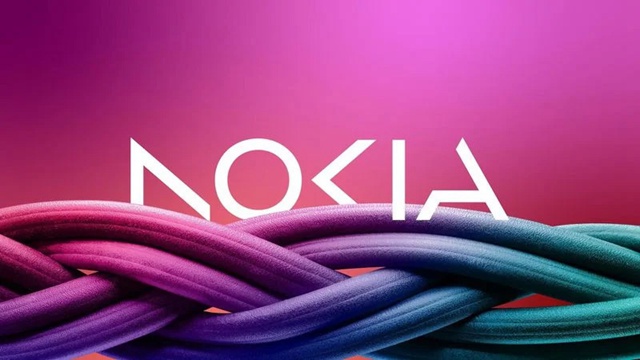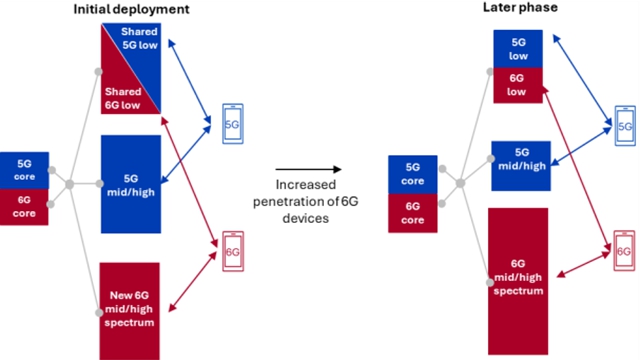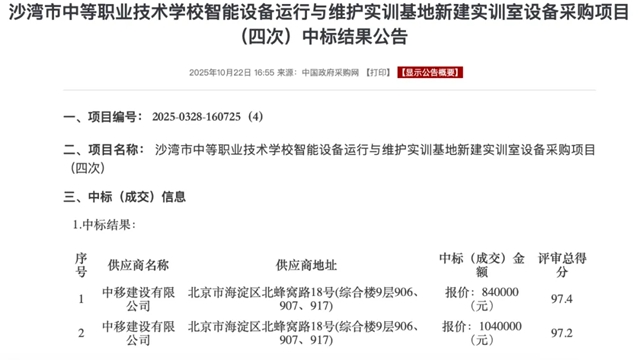全球化经济范式大转型时期,Google在数字空间对民族国家发起挑战,是一种必然。
“Google事件”发生之后,美国政府迅速回应。声明发表当晚,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即表示对该事件“深感不安”,“希望北京对Google邮箱被渗透一事作出解释”。奥巴马新闻秘书罗伯特·吉布斯也强调,总统高度关注此事。
一周以后, 1月21日,希拉里在美国新闻博物馆发表了“互联网自由”的演讲,呼吁将“技术进步”与美国价值观同步起来,并对Google声明给予肯定评价,号召其他技术公司以Google为榜样,就全球性对互联网自由的威胁,做出积极行动。
希拉里此举迅速引起了中国政府和民间舆论的不满,纷纷指责Google与美国政府合谋对中国展开互联网外交,干涉国家信息主权。至此Google事件从一个商业问题演变成一个政治问题,从一个跨国公司的权益主张,演变成国家层面的意识形态对峙。
各种各样相互冲突、对抗的主张与批评充斥了媒体,构成这个互联网全球化时代最吊诡的舆论风暴,在吸引大量眼球的同时,又令人纠结万分。恰如英国社会学家马丁·阿尔布劳所说“面对这种对划时代的变化的体验,有一种深刻的矛盾,它使我们的公共话语处于一种语无伦次的境地。”
这种状态只不过表明了,人们面对全球经济社会范式大转型时期错综复杂、矛盾纠结的严峻现实,都还没有做好准备。
互联网自由的国家逻辑
当人们为Google声明迷惑不解,对美国政府迅速介入感到惊讶,甚至怀疑在互联网问题上向中国发难可能已成为美国政府一个“战略上的、有计划的行动”之际,显然对于美国这种选择背后的历史脉络和国家逻辑缺乏清晰的认识。
美国的自由理念向来与一种对信息政策的理解密不可分,美国人把信息视作所有人共有的社会财富。事实和思想不属于任何人,也不应被压制、审查或监管,而应当被发现、传递、并在思想市场上自由交易。阿尔弗雷德·钱德勒因此指出:“信息在美国社会中扮演了一个非常特殊的角色,美国人将信息视为构成其社会、经济和政治世界的关键基石。”
这种信息自由传统可以追溯到美国建国之初。1760年代北美殖民地反抗英国政府的商业监督、税收控制和舆论审查之际,就成立了“通讯委员会”,并将“培养知情公民”当作对大英帝国议会立法抗议的目标之一。本杰明·富兰克林、乔治·华盛顿等革命家通过报纸、小册子发表意见、传播信息,动员民众摆脱大英帝国统治建立一个崭新国家。这是北美社会信息自由主张的先声。
后来的美国独立战争,就是在“通讯委员会”的领导下展开的。独立战争结束之后有关“公民知情权的”承诺被写入各州新宪法及联邦宪法的条款之中。之后的宪法第一修正案,明确提出保护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这是18世纪美国人政治觉悟的核心内容,也是建立合众国的核心力量。
正是在同样的价值观和使命之下,美国独立后本杰明·富兰克林出任邮政部长,建立美国邮政系统。美国国会颁布了《1792年邮政法》并予以财政补贴,支持邮政服务以低廉的费用和较快的效率将印刷品信息快速传达整个国家,促进信息自由流通。
钱德勒把这视为是美国信息高速公路的开端。并且把由此引发的持续300年的信息革命,当作是驱动美国国家转型的根本力量。后来的19世纪的铁路、电报、电话,以及20世纪的广播、电影、电视、计算机和互联网,都是这一基本逻辑的延续。300年来,对信息自由的主张和对信息自由对驱动国家转型、社会进步的信念一直是美国社会的基本共识。
一直到1993年克林顿和戈尔提出信息高速公路计划,互联网高速发展,信息产业因此成为驱动全球化的主要力量,美国推行信息自由的国家逻辑就从来没有改变过。希拉里·克林顿如今对互联网自由的主张,不过是其国家逻辑的一贯延续。
在某种意义上,希拉里“互联网自由”的讲话恰是十几年前戈尔“首先将人们置于信息时代”演讲的翻版。那时候戈尔也明确提出“我们不应把信息产业本身作为发展的最终目的,而应当把它作为一种被用来创造经济效益、提高生活水平和加强人类最基本价值准则的工具。数字时代对我们最重要的贡献不在于产生了新生事物,而在于复兴了旧的价值观念。”
正是这样一套理念及其统摄的治理框架下,美国的信息服务业获得了快速发展,成为美国过去十几年来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并使美国成为世界上头号信息产业强国。美国不仅孕育和培养出诸如微软、苹果、惠普、甲骨文、Google等一批世界上数一数二的信息服务企业,而且主导了全球信息产业技术标准、抢占了信息技术创新的制高点,有效地强化了国家竞争力,巩固了和提高了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
到2007年,全球信息产业规模约为46490亿美元,美国的信息产业规模已经占到球的40%。信息服务业已经成为美国最重要的战略性产业之一。2009年奥巴马上台后推行的经济改革计划核心除了启动新能源革命外,最重要的一部分即继续推进和深化信息产业革命。
希拉里“互联网自由”的主张与美国国家战略是一致的,那便是巩固并加强美国信息服务产业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主导地位,为美国互联网公司的全球化布局提供政治支持。
实际上,在2006年2月美国国会就通过了《互联网自由法案》,这部法案目的就是“促进互联网上的言论自由,保护美国企业”。该法案明确指出“通过互联网迅速提供充分及未经审查之信息,业已成为美国主要产业之一,亦是其主要出口产品之一。互联网政治审查会降低服务质量,并最终威胁美国国内外产业自身可靠性及生存力 。”
而且在该法案主导下成立了隶属于国务院的全球网络自由办公室,明确提出“推动通过任何不受限制的媒介获取和传播信息、思想的权力应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所有美国载体影响力,包括外交、贸易政策以及出口管制等手段,支持、促进并加强促进信息自由传播的原则、做法和价值观;禁止任何美国企业参与限制互联网自由国家的对网络内容的政治审查行为。”
在《互联网自由法案》约束下,奥巴马访华倡导“互联网开放”,Google提出“重新审视中国商业运营”,希拉里重申“互联网自由”主张,一点也不令人奇怪。恰如希拉里在演讲中所说“推动这一计划,将我们的原则、经济目标和战略优先级统一到了一起。”
Google事件既不是单纯的商业问题,也不是一个单纯的政治问题,而是一个互联网全球化处境下的政治经济学问题。
全球化以及来自公司的挑战
当初克林顿和戈尔提出信息高速公路计划之时,美国国会议员爱德华·马基说“来自华盛顿的好消息就是国会里每一个人都支持信息高速公路的提法。坏消息则是没有人知道它意味着什么。”
身处历史变化中的人们并不总是能够看清楚变化的意义。然而,迈克尔·哈特则从长的历史谱系中为我们揭示出这一变化的意义。
在《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一书中,迈克尔·哈特认为从中世纪以来,经济范式经过三次转变,每个范式均受主要经济部门的界定:在第一个范式中,农业原料的开采是经济主体;在第二个范式中,工业与可持续商品生产占据优势地位;而目前的第三个范式中,提供服务和掌控信息,则是经济生产的核心。范式的转变就经济核心的迁移过程;经济现代化即从第一个范式到第二个范式的转变过程,现代化即工业化;而从第二个范式转变的过程,即信息化。这与钱德勒将人类近代史分为三个时代即:商业时代、工业时代和信息时代的划分虽有差别,却又殊途同归。
哈特认为,信息化进程,从20世纪70年代就已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发生了。经济重心从工业向服务业迁移,这个经济范式的转换,引起了全球范围内的产业分工重组和产业格局调整,其结果是形成一种新的全球秩序。